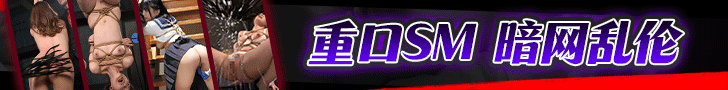落仙楼是晚上做生意的地方,华灯初上,脂粉飘香,楼中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湛子承躺在床上无聊的看着房顶,这楼板不厚,隔壁小倌正在接客,床铺吱呀吱呀,伴着阵阵娇喘声,搅的他谁也睡不着,躺也躺不下。
那天回来,就有人将他贞锁的钥匙送了过来,如今已经摘下数天了。
手伸进里裤中,抚了抚自己有些勃发的性器,隔壁的小倌叫的他心里发痒,让他想起之前帮凤年揉穴的时候,凤年的软叫,声音的比这小倌还好听。
他想起了凤年情动时湿漉漉的眼眸,裹着他手指不放的小穴,还有被按的流精的玉茎,他们两人肌肤相贴,贞锁也总是互相磨蹭,凤年流出来的都蹭到了他的锁身上,搞的两人胯间都黏黏糊糊。
凤年······
湛子承侧过身,将脸埋进枕头里,没有任何束缚的性器已经胀到了最大,粗硬的柱身上青筋狰狞,他撸动的动作越来越快,快感在小腹聚集,很快手心一热,已然是出精了。
快感只有那么一瞬间,稍纵即逝,剩下的就是无边的寂寞。
湛子承擦了擦手,无神的看着头顶的木板,虽然射了出来,但是这种感觉就像例行公事一样,射不射出来,区别也不是很大。
其实他之前也甚少自渎,偶尔来那么一次,感觉还不错,但是现在他已经找不回之前的感觉,反而跟凤年抱在一起的记忆越发清晰。
隔壁的小倌叫的声音只增不减,一声赛过一声,只是这声音听着怎么越来越奇怪了?
湛子承回过神,仔细听了听,发觉那声音已经不是叫床了,明明是在叫救命!
做小倌,被客人欺负是少不了的,湛子承在楼里这些天,见识到的也不少,但是不知为何他想起了那天凤年的哭喊,心里一揪,穿衣下了床。
隔壁的门只是虚掩着,湛子承抬手敲了敲,装着楼里龟奴的口气朝里面喊了一声:“客官,外面有人急着找您,您要不要出去看一下?”
里面晃床的声音骤停,一阵骂声传来:“哪个不长眼的现在找我?告诉他老子现在没空!”
“好嘞!”湛子承在外面蹬蹬故意走了几步,停了半晌,又走回门边:“那人说之前欠了您银子,今天赌钱赌赢了,手头富裕,想跟你清清账,他说您要是忙的话,就改天再找您。”
“改天?改天他还能有钱还我吗?”屋里想起一阵窸窸窣窣穿衣的声音,那人边穿边骂:“这个赵老四,真会挑时候,今天非让他连本带利的给老子结清楚。”
屋门吱呀一向,一个人影就从房中冲了出来,看也没看旁边的“龟公”,只朝楼下冲去。
湛子承在一旁低头垂目,等那人走远了,闪身钻进屋中,只见床上趴着一赤身裸体的小倌,两只手被绑在一起,身上青一片紫一片,他又仔细一看,只见那小倌的脖颈间一片乌青,想来是被那客人用什么勒了脖子。
这客人怎么如此狠毒,在床还要掐人脖子!
他将那小倌的手解开,把人翻过来,探了探他的鼻息,虽然气息微弱,但是没有什么大碍,应该只是一时昏过去了。
但是就这么放着,万一那客人回来,这小倌还是凶多吉少,这个屋子不能再呆了。湛子承将人抗在肩上,准备换个屋子安置他,刚推开房门,眼前竟站着一个人,湛子承以为客人这么快就回来了,吓了后退两步,定睛一看,这不正是凤年?
湛子承干了什么,凤年在不远处看的清清楚楚,此刻见他抱着小倌出来,这心里就觉得不痛快,只觉得他那手放搂着别人的腰怎么看着这么刺眼。
他冷冷撇了一眼,涂着口脂的朱唇轻启:“您这真是活菩萨在世啊,救了一个小倌不够,这是救上瘾了?”
两人虽然同在落仙楼,但是不只是谁躲着谁,这么多天愣是一面都没见。
湛子承看着浓妆艳抹的凤年,竟然感觉有些陌生,将肩上的小倌又抗了抗,老老实实说道:“那个客人下手不知轻重,我怕他死了,反正也就顺手的事儿。”
凤年想起之前自己干的事儿,心里有些虚,退后一步给他让出路来,朝一个屋子指了指:“那个屋子没人用,你把他放那儿吧。”
湛子承赶忙过去,等将人放好,才朝凤年道谢。
“凤年,你要去干什么?”湛子承见凤年要走,心里忽然感觉空落落的,他不知道凤年这几天都在做什么,是不是会跟客人······
“做小倌的,当然要接客了。”凤年摸了摸头上插的朱钗:“拜小将军所赐,奴家现在是个货真价实的小倌了。”
湛子承皱眉:“明明是你骗我在先······”
凤年挑眉:“骗你又如何?谁让你那么好骗,湛将军威名在外,没想到他儿子是个见小倌哭就走不动路的花花公子。”
之前也没觉着凤年说话这么呛人,湛子承凛然道:“救人怎么就成了花花公子了。”他指了指屋里小倌:“难道我就看着他死在我面前?”
湛子承声音稍大,
凤年心里就带了点委屈:为了那小倌你就吼我?就那么喜欢?
他看了看自己染的嫣红的指甲,声音越发凉了:“小倌不就是个给人玩的东西,死了就死了,这世间小倌这么多,你救得过来么······”
“小倌也是人!”湛子承猛然上前,抓住了凤年的手腕,气到:“我看见了,就不能见死不救。”
凤年一怔,被湛子承看的心里咚咚直跳,过了半晌才缓过神来,“你放开我!”,湛子承捏的也不紧,他愣是抽了两下才将自己的手抽出来,忙要转身逃开,不妨被人拦了路。
“这美人儿之前怎么没见过?”前面一穿着明黄锦袍的人走了过来,直接拿扇子抬起凤年的下巴,仔细端详了半天:“啧啧,看着小样儿还挺犟。”
一旁的魏三见着了,赶忙也走了过来:“关爷,这位早让人给包了,只陪酒,不能近身,楼里娇花多着呢,小的给你换个好的?”
他自从被上头吩咐了要让凤年吃点苦头,又不能让他真的去接客,也不知这凤年到底什么身份,若是普通的小倌也就算了,偏偏这凤年长了一张头牌的脸,就算这人臭着脸往客人旁边一坐,什么也不干,就把一帮人整的五迷三道,恨不得眼珠子都黏这小妖精身上。
这一场场酒陪下来,十个有八个悄悄跟他打听价钱,剩下两个有点权势的,那当场就要拉人进包厢快活,哪管你卖不卖身,老子今天就是要干了你!
为了这事儿他给人陪了多少不是,挨了多少白眼,自从被调到这楼里当个管事,还没像现在这么憋屈过。
偏偏那凤年还一点不领情,每次他跟狗一样把围着他的那些客人哄走,人甩甩袖子就回房了,连个眼神儿都懒得给,嘿,真是出力不讨好。
这关奇文是城里关员外的小儿子,那是楼里老主顾了,出了名的霸道,看上了谁那是非要拉自己床上才罢休,这要是缠上了凤年那还得了。
他朝凤年使眼色:赶紧走,别添乱。
凤年撇过头,手背嫌弃的擦了擦下巴,像是被什么脏东西碰了一样,看也不看关文奇,转身欲走,谁知那人却跟狗皮膏药一样贴了上来,再次拦住他去路。
关奇文一收扇子,将人上下打量了一番,凤年腰细腿长,肤白貌美,特别是那一朵朱唇,勾的他只想一亲芳泽,魏三越是拦着,他更加不想放手,眼珠子转了转,便一脸大度的说道:“既然如此,关某也不能让你难做,让他过来陪爷喝两杯,这总可以吧。”
魏三怎能不知他心里想的什么,忙又打哈哈:“哎呦今儿还真不凑巧,有客人已经点了······”
“那就给拒了,爷出两份儿钱!”关奇文懒得再跟他费口舌,直接勾起凤年腰间系带朝自己包间走。
凤年被扯的一个趔趄,头上朱钗乱颤,差点被自己繁乱的衣摆给绊倒,他若是真不愿走,十个关文奇也拉不走他,但是他现在是楼里小倌,就算不卖身,这关文奇口口声声说只让他陪酒,他也只得松了力道,跟着腰间力道朝前走。
这是那位大人的惩罚,他不敢不听话。
关奇文顺势将他搂入怀中,带着进屋了。
魏三见拦不住,生怕关奇文真把人给办了,只好陪着笑跟上去,走到门口又被推了出来,门内传来关奇文不耐烦的吩咐:“一会儿我有朋友过来,多叫几个陪酒的,再拖拖拉拉,别怪关爷我不给你面子!”
魏三苦着脸答应了一声,心里正想着一会儿找谁帮他看照,一抬头就看见了在那杵着的湛子承。
又是个惹不起的。
这湛子承之前还跟凤年黏黏糊糊,自从出楼接了一趟外客,也不知怎么的,两人就突然生分了,不住一个屋也就罢了,连面也不常见,不知他们到底闹了什么别扭。
“三爷,这位客人需要人听琴吗?”湛子承自从得了自由身,虽说明面上还是楼里的琴师,对魏三的敌意倒是没那么大了。
魏三瞅了他一眼:“你不是跟凤年吵架了吗?”
湛子承错开眼:“这哪里的话。”他明明知道凤年之前都是跟自己做戏,但是午夜梦回,那肌肤相亲的感觉却总也忘不掉,如今见他不情不愿被人带走,就只想跟上去,生怕他出事。
拿着糖葫芦少年的身影渐渐在他心中淡去,凤年一边喘息一边叫着子承哥哥的样子倒是经常从心底冒出来。
“啧啧,都是楼里的奴,能有个互相照顾的不容易,有什么事儿说开了就好,这楼里的人你今天还见着,明天就不知道被什么人买走,见一面少一面啊。”魏三叹了口气:“这关爷不好伺候,凤年今天怕是要吃苦头,一会儿我把你塞进去,你帮我看着点儿,千万不能让关爷把他拖床上,有什么事儿赶紧过来找我。”
这话你不说,我也不会让凤年跟他上床···湛子承朝魏三弯了弯腰:“谢谢三爷。”
“咳。”湛子承突然这么恭顺,让魏三还有点不习惯,他后退一步摆摆手:“回去拿琴吧。”
===============
屋内
几个客人一人搂着一个小倌,酒杯相碰,不时发出阵阵淫笑。
湛子承和几个奏乐的混在一起,手上规规矩矩的弹琴,眼睛却不时朝关奇文怀里的凤年看几眼。
“美人儿,这都喝了半个时辰了,你怎么还不肯笑一笑,再皱眉头,都要变丑了,哈哈哈~”关奇文攥着凤年的脖子,将酒杯举到他唇边,凤年躲不过,只好顺着喝下,关奇文灌的太急,烈酒辣喉,呛的他低头咳喘不止。
他本就生的极美,轻咳之间,眼角微红,玉手轻掩朱唇,一缕酒液缓缓从下颌滴落,狼狈之间也生出无限风情。
众人见此又是哄笑,一人起哄道:“关爷,这美人太冷,不如脱了他鞋袜,用羽毛挑他脚心,看他还如何拿乔?”
关奇文立刻大赞:“这主意好!”赤红着脸将桌上杯盘一推,腾出来一个空地儿来。
凤年还咳着,就被提着腰带按到桌上,惊呼一声,右腿已经被人高高举起,没有穿里裤的下半身一时春光大泄,含着玉势的菊穴和下方贞锁尽数展露人前。
“啧啧啧!”屋里响起一阵惊叹之声,这香艳场面把周围几人看的欲火焚身,若不是关奇文霸着,恨不得立刻扑上去,将他分吃干净。
关奇文也被眼前美景迷了眼,忘了自己把人按桌子上准备干什么了,痴痴的伸手摸上眼前的雪臀,狠狠一掐:“这小婊子,屁股真白!”
凤年趴在桌上,一眼看到了不远处抚琴的湛子承,四目遥遥相对,凤年难堪的垂下眸,指甲已掐入手心。
曾经被摸过多少次大腿,被人占有过多少次身体,凤年记不清,也懒得记了。曾经的他不会感到羞耻,只会默默的几下这些人的名字,在爬上高位之后,给他们一个个安排个精心挑选的死法。
但不知为何,被湛子承看着,他竟然有种被玷污的错觉。
真是奇怪,自己早就已经不干净了,何来的玷污呢?
凤年眸中蓄满清泪,慢慢溢出眼眶,滴落在自己手背上:偏偏就是···不想被他看到自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