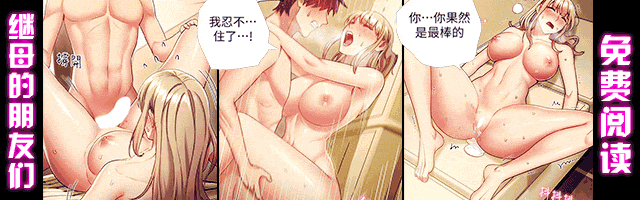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这是干什么用的,怎么还多了一个?”荀七直起身子抻了抻胳膊,从琴凳上拎起一只黑色胶皮套子,拿在手里晃了晃,目光饶有兴致地看向下方。他的奴隶安静地跪在他腿边的地面上,赤裸的身体几乎完全隐没在覆满全身的黑色胶衣里,只在外面显出流畅平滑的曲线。
这件压箱底的衣服,他之前一直嫌麻烦懒得研究,今日兴之所至,就忍不住想尝试点新的玩法。黑色的胶衣紧紧裹上奴隶光裸的皮肤,把奴隶装点成不同以往的模样,手指抚过去,指下传来别样的触感,倒是确实带来了不少新鲜感。
“主人,这是用在胳膊上……”玲珑大腿分开跪坐着,腿根几乎贴到地面上,大小腿折叠着被绑在一起,束带系得极紧,压制了一切挣扎的可能。他把背在身后的胳膊伸直,双手对扣,从大臂至小臂都紧紧贴在一起。韧带被撕扯得生疼,他的声音因为隐忍而夹了一丝不易察觉的轻颤,“像这样套起来,就动不了了。”
随着双臂的贴合,他的肩膀被狠狠向后拉开,脖颈不由自主地微微上仰,胸膛进一步挺起来,呈现出完全的展示姿态。
“好主意。”荀七居高临下地看着奴隶的样子,轻飘飘点头赞了一声,接着重又弯下腰,把黑色的皮套戴在奴隶的胳膊上。他快速把系带穿过并在一起的两排环扣,又把带头来出来狠狠抽紧,娴熟地打上不易挣脱的结,接着用手指耐心地抚平胶衣上所有细小的褶皱和不够贴合皮肤的隙腔,再把各处拉链逐一封好。
随着系带被抽紧,玲珑的肩膀进一步打开,两条紧绷的肩线斜斜向后延伸,顺着手臂一路疼到腿根。胶衣带来的束缚感十足,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他痛苦地轻轻蹙了蹙眉头,又迅速舒展开,慢慢放缓呼吸,克制着挣扎的本能,尽量以最驯顺的姿态配合荀七一点点剥夺他对肢体的所有控制权。
这套衣服来自星月馆,尺寸自是严丝合缝。荀七拉好最后一条拉链,站起身打量了片刻,满意地确认奴隶身上的衣服已经彻底穿好,于是伸手去够放在一旁的头套。
玲珑微抬起眼睛,目光追随着主人刚刚在他身上流连的手指。半暗的灯光自斜上方照下来,穿过细密的长睫,在他苍白的脸颊刷上不安的颤影。他的喉头轻轻滚动了一下,嘴唇抿出湿漉漉的痕迹,略微张了张,又重新闭紧。
他与主人相处日渐默契,胆子也大了不少,平日里撒娇求饶已经颇算得上熟练。可今夜,主人的情绪实在让他捉摸不透。
静下心来细细回想,主人回家时心情分明不错,还有闲心搂着他用不着调的诗词调笑……想到这儿,他极轻地向上勾了勾嘴角,心跳似乎隐秘地快了一个节拍,但只一瞬,就又重新沉落下去。
就是现在,主人似乎……也不像是动了真怒。然而上次得的教训太深太狠,心上还栓着道解不开的题,此刻他不敢太过相信自己的直觉。
应当还是他做错了什么,再一次惹怒了主人——仅仅是转过这个念头,都让他忍不住轻轻打了个哆嗦,觉得浑身发冷。或许是这几日他仗着主人纵容,太过忘乎所以,更或者……他的牙齿合在下唇内侧的软肉上,勉强压下愈发纷乱的思绪,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眼下。无论如何,有一点毋庸置疑——他的主人确实起了兴致。
那么,不管是使用、玩弄还是惩罚,服从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只这一个愣神的功夫,荀七已把头套扣上奴隶的脑袋。紧绷的皮套压迫喉管,嘴唇亦被紧紧压在胶皮底下,鼻下只留出了一点小孔,玲珑的呼吸陡然变得艰难起来。眼前失去了光亮,耳畔也没了声音,他的全身都被裹在粘稠暧昧的黑暗里,所有的感官都迟钝起来。肢体不受掌控,连知觉都迅速变得模糊,只有从被压迫的韧带处传来的绵密又清晰的疼痛,不住提醒着他这具身体正在被谁掌控。
然而即使理智清晰地知道主人就在身边,不安和惶恐依然像黑色的潮水,缓慢又不可阻挡地漫过麻木的四肢,又在瞬间淹没口鼻,几乎夺走呼吸。在陡然笼罩下来的漆黑和寂静里,噩梦复苏,恐惧抬头,被刻意遗忘在深渊里的不堪回忆像一株妖异的藤蔓,攀附着血肉悄然生长,只等着天光被云翳遮住的刹那,就要在阴影里露出獠牙来。
耳边似乎响起极细微的脚步声,却又缥缈得仿佛幻觉。一时间,就连主人的存在也变得模糊起来。
不,别走……别把他丢在这……
玲珑的唇瓣翕动了一下,被贴合面部的胶皮紧紧束缚着,任何细微的活动都变得艰难。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发出了声音,颈间的系带却似乎在无声地收紧。
“奴隶,学不会取悦主人,你就毫无价值。”调教师不带一丝感情的冰冷声音像是就响在耳畔,清晰得刺骨,“想拖时间?那我们换一种办法。”
不……他已经学会了……他已经记住了,不要——
“记住这种药的名字,它叫‘相思’。”一声轻笑,带着丝淡淡的嘲弄,“不过想来你想忘也忘不掉。听说你读过不少书,那么应该很快就能懂了。”
不,求您……碰碰我,谁都好…
…先生、主人……
身体里有无数春蚕在破茧,又挣扎着扑进熊熊烈火中。他从来不知道,原来欲望也可以变成刑具,而脆弱的血肉之躯对此无可抵挡。
“救我……求你别走,救救我……”他听见自己的声音,隐忍绝望,带着颤抖的哭腔。他无声地张开嘴,却怎么也吐不出想要的句子,就像时间终不可重来,而过去总会固执地留下痕迹——
救我,主人,求您带我走。
……
荀七调整好头套的位置,抽紧系带,系上最后一道拉锁,接着起身走进客卧。他的目光在柜子里码放得整整齐齐的道具上逡巡片刻,挑了只颜色顺眼的木拍拿在手里,然后迈着轻快的步子走回厅里。他的奴隶仍然跪在原地,维持着分腿挺胸的跪姿,与他离开时没有任何区别。
不,还是有什么不一样了。
他轻轻皱起眉头,快走几步,把手拍放在琴凳上,屈膝半跪下来,双手握住奴隶不住颤抖的肩头。手掌下的胶衣滑腻柔软,却让他忽然怀念起奴隶皮肤的温度。
似乎感受到他的触碰,奴隶的身体猛地震了一下,之后飞速向他靠近,明明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清,却十分精准地靠上他的手臂,如果不是腿部被折叠绑缚着移动不便,几乎就要直直撞进他怀里。
荀七一只手握着奴隶肩头,另一只手缓缓捋过奴隶的背,手掌重重压下去,又揽上柔软的腰身。被他的动作安抚,奴隶的身体安静下去,却仍然依恋地倚靠着他,不肯自己跪稳,被紧紧包裹的胸膛剧烈起伏着,喉间发出细弱的哀鸣。
荀七轻轻眯起眼,隐约猜到发生了什么。他也不耐烦去解繁琐的死结,却也决不允许奴隶在这个时候“走神”。好在,他擅长的,向来都是“一刀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