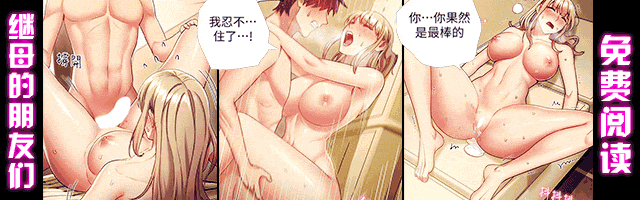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军方和世家起争执期间,佛寺代世家保存了部分物件,其中便包括张施主母亲的灵芯,”隰桑在桌台边站定,“她在张家时向家主索要,可家主没放在心上,一直以为灵芯已遗失。后灵芯被夹在书册里,送至醴乐寺,锁在藏经楼,但是如无张家家主密钥,任何人不得从中取物。”
“师父硬闯了?”这极像她的风格。
隰桑摇摇头:“头一次,她找贫僧商议,用另一件物品换取灵芯,贫僧并未应允。”
“出家人不是讲究慈悲为怀吗?隰桑大师为何拒绝?”这与李欲何的认知稍有偏差。
“贫僧职在守楼。佛寺先允诺于世家家主,不可不守约。”
“所以,第二次她就像我一样,偷偷来破阵?”李欲何猜测。
“第二次,张施主潜入醴乐寺,破阵偷走灵芯,还损毁了寺中的金身佛像。这就是她不受佛家欢迎的缘由。”隰桑的声音里听不出怒气,但显然这情绪不是赞扬。
果然,师父还是厉害得多,李欲何强忍笑意,拉过木椅坐他斜对面:“那大师怎么会救她徒弟?”
“贫僧守规矩,并不意味着贫僧不近人情。”
“您不是修无情法门吗?”
“非也,”隰桑拨弄几下手中的佛珠,“佛陀应世,旨在为众生解除苦难,此乃‘大情’。我斩的情是‘狭情’,是‘烦恼’,需从中解脱,方能得证圆满。”
“那我好像已经成为了您的‘狭情’或者是烦恼,”李欲何打趣道,“性格上,我和师父一脉相承,您得早些把我斩断。”相处一会儿,气氛渐渐变得轻松,他觉得这僧人也并没有成则说的那么无情可怖,只是总端着个冷冰石雕似的姿态,有些无聊。
“佛门中人永远把‘大情’放在‘私怨’前,隰桑百年前便断除‘执’根了。”
“百年前?”李欲何闻言惊讶不已,“那您……”
“二百三十岁整。”
“哇,看不出来,都没皱纹。”李欲何没了畏惧之心,起身到他下方抬头观察——之所以称“下方”,是因为这僧人站着就跟铜头罗汉似的,形体足足比他大一圈,他站直后,头顶还够不到他下巴。
“这么些年过去,欲何施主依旧宛如孩童。”隰桑退后一步,生怕他又不慎撞到自己胸口。
“等等,”李欲何在空中嗅嗅,疑问道,“大师,我在来藏经楼的途中就想知晓,为什么我总对您有种熟悉感?是白玉菩提子的缘故?”这种熟悉感比单纯的“见过一面”或是“听过几次声音”深刻得多,就好像他们相处许久,且一同历经过无数变迁。
隰桑回拨几颗佛珠,半晌不答。
“告诉我好不好?反正您都说那么多了。”李欲何冲他笑笑。
“那欲何施主能否告诉贫僧,你此次来醴乐寺是何目的?”隰桑岔开话题。
“您先说,我再说。”李欲何不上当,一定要等到答案。
“这并无意义。”
“你的问题更没意义,”李欲何把往下垮的僧袍往上抖抖,“刚给我换衣服的时候,不信你没看到!淫纹,女穴,见多识广活了二百三十年的隰桑大师肯定瞥见就立马辨识出了吧?”他被打捞上岸时,浑身湿漉漉的,然而转醒时,他的全身包括下体都被人擦得干净清爽,还换上了不知是谁的僧袍——这屋里就他俩,总不可能是他自己在梦境中完成的。
隰桑的眸光难得地有一瞬波动,他再退后一步,索性持着佛珠默念经文。
“大师?”李欲何追上去,扯着佛珠不让他拨。
隰桑用另一只结印的手去拉他手腕,但那金刚体稍一用力,就把他白皙的手背按出几道深红的血印。
“嘶……”李欲何疼到抽气,却仍不肯放。
“欲何施主!”隰桑忙从他手背移开,又走到进门的木柜旁,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瓷瓶。他回来时眼带愠怒,可这怒气并非针对李欲何,而是他自己。
“您的‘狭情’白斩了,”李欲何见他生气,不怕反笑,“怎么还跟个世俗界凡人似的?”
隰桑打开药瓶,小心翼翼握住他的手,把一撮褐色粉末洒在他被按伤的地方,又施咒将它润湿。药粉很有效,敷上一两分钟,深红就转为淡红,随后,药粉被全部吸收,伤痕消隐。
“白玉菩提子……是不是在你身边贴身保存了很久?”李欲何盯着他绕在前臂的佛珠,蓦地有了猜想。
隰桑没予以肯定,但从他动作的僵硬程度看来,这猜测估计靠谱。
“大师,你说说你,怎么做好事还遮遮掩掩?难道当初是一时冲动才把它给我的?”他可真是个怪和尚。
“佛缘。”隰桑总算舍得开口。
“嗯?佛缘?”
“贫僧以为,欲何施主有慧根,炼化过的菩提子可助施主得到佛缘,入我寺修佛,”他缓缓述说,“未曾想,你的执念太深,它无法引你入法门,反被磨得只剩灵芯。”
李欲何用现代思维思考一阵,彻底理解了:这不就是你用大量财物或者利益去外地搞人才引进,哪知那人稀里糊涂拿完你的好处,反而跑到了其他阵营?确实有点儿丢份,怨不得人家不直说。
“我……还是不剃光头比较合适,”李欲何“心有余悸”地摸摸自己的头发,“长是长了些,也比没头发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