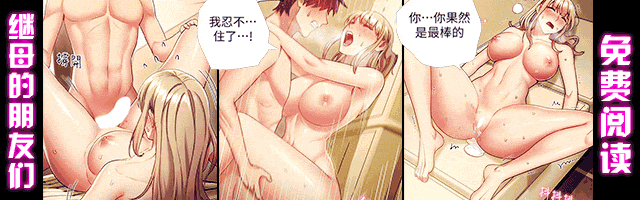朱尧姜本就在细细观察扶风,见状,悄悄给宫侍递了个眼色。
那宫侍立刻奉上布帕:“小郎中请用。”
扶风赶快拿着擦了汗。
忽然,里侧酣睡的十二皇子嗷嗷大哭起来,娴贵君立刻抱起来哄了哄:“你们都在这里伺候着皇主,本宫喂福王。”
“是。”
待娴贵君抱着十二皇子去后殿,朱尧姜轻轻开口。
“我名唤尧姜,封号是父皇所赐的仙蕙,小郎中可有字号?”
听朱尧姜这般问,两个人挨着的也近,扶风只觉得朱尧姜身上的体香和呼出的兰香把他都给迷晕了。
“小的不曾出师,师父不曾给字号。”
朱尧姜微笑,语气有些稚音说出的话却很是成熟稳重:“不久,你也会和你的师父一样,成大器,你们都是好大夫。”
顿了顿,朱尧姜回头看娴贵君没回来,转头俯身,眼瞳极认真:“你们都是好大夫,好人,以后,不要再来了,此是非之地不久留。”
扶风挺感激的,感觉到他的好意和隐晦的提醒:“我与师父草民两个,身不由己,还是多谢皇主提点。”
奇了怪了,他之前伺候朱尧姜,怎么没感觉朱尧姜这么善良美丽?
朱尧姜苦笑,他也不能直接向着外人,背叛自己的阿姆,娴贵君与他,十皇兄,十二皇弟,他们父子三人已经是烈火烹油,自身难保,不得不做出一些事情。
但,楚江和扶风他们师徒,是救了自己和阿姆的恩人啊!
扶风给朱尧姜开了药后,带着娴贵君殷殷切切的问候和礼物出宫。
到了民居小院,扶风一阵风般的跑进前堂屋,把礼物扔给碧桃、红叶。自己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对着在堂屋坐着边和舒晴方下棋边泡脚的楚江兴高采烈的嚷嚷。
“师父!师父!太医院正院判黄槐被撤职入了大狱!他弟弟黄桧也贬为普通御医了!还有娴贵君生的十二皇子也封为福王了!”
楚江淡定的很:“哦。”
“徒弟不知啊,师父,您怎么一点都不吃惊?”
一旁的舒晴方虽说是和楚江下棋,但眼神时刻盯着楚江的脚看。‘啪’地落下一子,柔声问:“夫君,要不要加些热水?”
“不用,现在还热乎。”
扶风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师父,师姆,你们都……”
舒晴方冷冷敛合浓密绒绒的长长卷睫,石榴籽儿肉般的红唇抿着,带着一股子轻蔑和了然:“夫君,你遇刺一事,上面那位一定知晓。”
“那是一定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何况还在皇
城的地界儿,娴贵君如今美貌再复,宠冠后宫,九皇主也要和平西王世子联姻,一个爱妃,一个爱子,枕头风吹着,小棉袄披着,这么久了也没见皇帝处置后君和太子,能动太医,能封王,也是我受伤的事儿被吹风吹了过去。”
扶风明白他们夫夫说的话了,凑到楚江身边儿:“可是师父,我瞧着,未必是他们姆子吹的,其实九皇主今天还好心提醒咱们不要去宫里呢。”
楚江冷笑:“你个傻小子,不是未必,我遇刺就是娴贵君他们指使,牺牲我一个,能让后君和太子的势力削弱,还能扮演苦主,对谁罪有益呢?”
只有娴贵君……
扶风皱眉,心里对朱尧姜也不喜了:“师父,这你怎么还挺高兴的?”
这不明摆着被娴贵君恩将仇报了吗?难道师父和娴贵君都暗中商量好了?
楚江专注的看着棋盘,心里哀叹又输给自家美人了:“我当然高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瞧瞧这会儿,虽然不痛快,但我省了多少事儿。”
他就是要利用娴贵君,利用韩棒阴,他才能全身而退。
舒晴方起身,走至楚江身边,挨着坐下,沉静低头,忽而抬起,似欲言又止,但还是没说什么,只给楚江倒了一盏牛乳茶:“夫君。”
楚江接了茶,一饮而尽:“皇帝对黄氏兄弟已经起疑,他们俩离死不远了,只要他们俩一死,我的事儿就了了。”
扶风从没见过报仇报的这么云淡风轻的,他跟随楚江学医多年,还是没看透楚江。
“那师父,咱们现在的事儿……”
“当然还没了,接下来就要韩棒阴公公出面了。”
扶风终于明白了,露出憨笑,十分佩服他家师父:“反正最后都不干咱们家半个铜板的关系,师父定然全都筹划好了!我现在就去准备好给韩棒阴做手术的物拾。”
楚江点头,伸手握住舒晴方细腻的手腕把玩一番,两只大手把小手包住:“从中作阀,借力打力。”
扶风不欲再做碍眼的,把楚江的洗脚水端了出去。
舒晴方轻轻靠在楚江肩头,浓密的长睫挡住眼里的所有情绪:“夫君之智,晴方自愧弗如。”
“我哪算什么智,尽力而为,如果不能保全自己,苟且偷生就偷生吧,这仇恨我也不亲手报了,并非贪生怕死,你和孩子比什么都要紧。你刚刚似有话要对我说,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楚江手圈着美人的腰身。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不能为了仇恨豁出全部,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活着才有希望,才有机会。
“夫君,我们互通互惠,一起借力打力,好不好?”舒晴方抬起睫羽,乌黑的瞳仁幽深忽明忽暗。
“好啊,我就等你这句话了。”楚江露齿一笑。
舒晴方贴上楚江的耳边,悄声说几句话。
楚江挑眉:“只如此?没有旁的?”
舒晴方玉般的嫩长手指整理楚江的后颈领口,眼珠裹着一层厚厚的水波,顺势勾住楚江的颈子,温柔道:“只如此,没有旁的,怕累着晴儿的楚郎。”
楚江啄吻一口美人翘起的红唇:“好。”
忽而挑眉,楚江又吻了一下美人雪白的腮:“好人儿,你头前应我的事呢?”
舒晴方脸烫,想楚江也的确在家中憋闷许久,眼珠更水润化开柔波:“待夫君痊愈,晴儿带夫君去。”
这厢楚江只觉杀师之仇已经报了一多半,一心只惦记着舒晴方那头。
毕竟他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晓。
谁料,没等到舒晴方带他去‘藕花深处’,何狐狸那厮倒是提着好些东西来探望。
进门倒不客气,挨着楚江坐在罗汉榻边:“来来来,可怜的楚兄,我特意带了好些红枣、桂圆、阿胶全都是补血的好物!啧啧啧。”
楚江不自在,他早好了,又不是坐月子,吃什么阿胶,起身去另一侧坐:“多谢何兄,你都出去接正君吧。”把红叶等佣人摒退。
舒晴方去药堂办事,他才敢放何九郎进门,这何九郎赶快说正事啊。
何九郎一脸的嘲笑不屑:“你个妻奴!没出息啊!堂堂神医比大理寺府尹还惧内。”
看楚江真的急了,何九郎不再逗他,神神秘秘道:“你知道,那天要杀你的人是谁派来的吗?”
楚江看着他:“谁?”
何九郎慢悠悠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狭长的眼睛挑起:“不错不错。”
“我告诉你,是两拨人。”
楚江拧眉,其中一波他知道是娴贵君,另一波又是谁?
何九郎笑眯了眼:“一波是陪王伴驾现在炙手可热的,另一波暂时未查出来,有些线索,我建议你去问问你家小夫郎。”
“他怎么会知道?”
“啧,其中一人咬破的毒丸是十年前修河堤时发掘的毒蚁提炼成的,那毒蚁现在在工部还有存档和标本。”
楚江疑惑的重复:“工部?工部的人没必
要害我。”
工部,工部与他这郎中八竿子打不着啊……工部。
何九郎阴阳怪气的嗑瓜子:“再想想,工部尚书周家,他们家的老二差点给你家美人当了乘龙赘婿。”
周琅。
楚江知晓了,脸色不好看,但冷静后,又想周琅现在每个月都需要自己的解药,而且受制于舒晴方,要是自己死了,周琅也活不了,谁会这么二?
何九郎似笑非笑:“你自己好好想想吧,对了哦,你那小夫郎开的雅妓馆名声越来越大,诗词歌舞乐器床技乃是五绝,穿的,跳的,唱的,当真是世所罕见,可以称为最新颖的雅妓馆了,我也算小哥儿和男子荤素不忌,就从没见过穿的那么大胆的雅妓,前儿我那便宜夫婿去看了,真真是不错,就是贵了点,还非得持贵宾名牌不得进,走了。”
何九满意的看着楚江面色越来越冰冷,抬脚便走。
“等等。”
何九郎驻足,卡巴卡巴眼,嬉笑着回来:“怎么,舍不得爷?”
楚江冷着脸:“藕花深处在什么地方?”
他一定要知道地点所在,舒晴方故意不告诉他,几日还早出晚归,怕是已经提前行动了,舒晴方会有危险!他不能再放任晴儿自由了!
这下轮到何九郎失声大笑,笑的眼泪都出来:“你哈哈哈……你太好笑了……你真是那小美人的夫君吗?哈哈哈哈……”
楚江心里烦躁,“咚”地把茶盏重重搁到桌台上,怒道:“你非要废话连篇吗?!”
“咔嚓——”薄胎玉瓷的盖碗瞬间破裂成三半。
何九郎笑声戛然而止,耸肩,嘴角冷意,眯着眼格外狡黠:“看你可怜,告诉你,城郊三十里亭外继续走,绕过香雪海作坊,红檀山庄前边儿……”
得知地点,楚江立刻起身,捡了搭在架子上的外衫大步往外走。
“哐当——”几乎是夺门而出,刚好开门撞上了在门口偷听的扶风。
扶风摔了个屁股蹲儿,尴尬的挠了挠后脑勺:“嘿嘿……嘿嘿嘿师父啊?要出门儿,徒儿给您备马哈?”
楚江黑着脸点头。
拿上马鞭,焦急跨马鞍,楚江调转马头,冷冰冰的勒令:“扶风你去药堂看看,回来哪儿也不许去,在家看门儿,等着我。”
“师父您伤刚刚好,让我跟——”扶风拉住缰绳,不放楚江走,很是担心他师父这怒气恒生的再出事,伤口再裂开,但楚江根本不听他的,夹马肚子,摔鞭子,飞驰而去。
“咴儿……咴儿……”
何九郎靠在门边,轻佻的对着楚江骑马离去的潇洒背影吹着口哨:“看来我并非一点机会也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