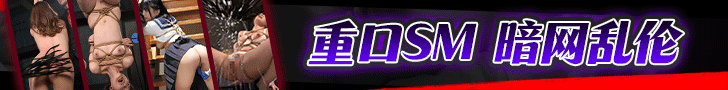戚涣回到沧云阁时天已近黑,此时正是一年最冷的时候,仙界少雪,零星一点都是为了给人看着玩,聚不成白色,没一会就化成了湿淋淋的冰碴,钻着骨缝的阴冷。
“仙尊。”
一个娃娃脸的少年小跑着过来,塞给他一个银手炉,接过他手中提的几坛酒。戚涣对他有点印象,应当是玄宗掌门的儿子,未及弱冠的年纪被父亲送到十八周天做了容恕洲的侍从。说是侍从,容恕洲也不需要一个孩子为他做什么,向来当弟子教的,平日里性子就格外活泼。
戚涣接过手炉“多谢,帮我将这酒温上。”说着取了个小荷包和几个小糖人糖果子一并递给那孩子。衣袖微动,袖口银线掐丝的繁复纹饰盛着冬日里冷清的阳光缓缓流淌,远胜三尺白雪。“糖里有竹签,当心些。”
“好嘞。”少年讨喜地笑眯了眼“谢谢仙尊!”
戚涣笑笑,看那少年跑远,忍不住将手臂向雪白的披风中收了收,苍白修长的手指覆在手炉的银罩上,指尖有了点绯红的活气。
他体质极寒,夏天还好,一到冬天就难熬些。也没少调养,可多年落下的病根,什么方子到他这都收效甚微。
他习惯了也不觉得怎样,倒是从下了第一场雪后,容恕洲就分外在意,以至于整个十八周天上下只要见他空着手,先如临大敌似的先找个手炉给他,再站好说话。
屋里也早早生了银炭,无时无刻不备着姜汤暖茶。
倒是的确管用,入冬这些时日,他竟一次高热也没发过。
那日听陆年提起听澜楼的四合酒,言语间多有怀念之意。可话赶话的事,谁也没想起来去买。
自从冗虚派封门闭宗,堂堂众合狱主亲自论功定罪,他这个名义上的掌门就做了甩手掌柜。各峰首领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事格外多,陈年旧例处理起来最是麻烦,饶是容恕洲手腕雷霆也忙了大半个月。
难得今天空闲一日,突然想起来这事,就想买些回来。没想到正值年关,人多得厉害,只是排队就耽搁了许久,路途又远,一来一回竟搭了一日进去,身上穿得多倒还不算太冷,就是手里要提酒,一直露在外面,冻得麻木刺痛。
戚涣穿过前庭,刚走到廊下就听到屋内有交谈的声音。知道应该是有客。
他与容恕洲二人倒是没有什么非礼勿听一说,但是既然容恕洲没有叫他,就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多半是哪个宗门纨绔的鸡零狗碎被清洗出来,来找容恕洲告罪以求宽宥。
这种地头蛇极难缠,常年夹在名门大宗之间过活,为了那些灵器机缘练就一副油嘴滑舌,两面三刀之流,他也没兴致和他们周旋。
索性往书斋走。
走了几步才想起来今天早上容恕洲说要去藏书阁找几个孤本,就顺手把钥匙放容恕洲那了。
只得又折回去。
从侧门抄了近道进去,就看见屏风后影影绰绰几个人影。
“圣尊,这是我们刚出阁的孩子,绝对干净听话。”
干净二字被着重咬过,个中意思不言而喻。
说话那人挺着肚子,一身绫罗绸缎,笑起来满面红光,正把一个俊俏的少年往前推。
那少年被推了一个踉跄,只穿了一件单薄的白衣,两襟交叠漏出大片凝脂似雪的肌肤。抬头看,眉目与戚涣有八分相似。
细看却又不一样。
戚涣看人时总带着浅淡笑意,微微一侧目便有万种惊鸿,端方和妖魅两种特性激烈地交织在一起,唇红齿白,如骄阳烈火,很容易引起人的摧残欲念。可他眸色偏又极重,彰显出一种格格不入的强硬漠然,那是苦难浸渍出来不可测的壁障深渊,铜墙铁壁后藏着万千退路和冰天雪地,谁也不得触及分毫。
而那少年是当真清冽澄澈,琥珀样的眼睛,通透热烈一眼就能看到魂魄。
那少年给容恕洲斟茶,洁白无瑕的手指覆在青窑上,荷叶团珠般青葱剔透。
容恕洲背对着戚涣,看不见表情。
戚涣悄无声息地退了出来,没有一个人发现他。
“不必了”容恕洲目光冷然,少年停住不敢靠近,怯生生眨着满眼企求看他。
容恕洲这才把目光转向那大腹便便的男人。
那男人见他的反应,知道大事不好,忙补救道“圣尊,我那府上还有不少漂亮孩子,什么都会,您若肯赏脸,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此事,汲,汲垣仙尊也绝不会知道……”
这什么都会自然是指各种奇淫巧技。
“闭嘴。”
男人被他修罗一样的脸色吓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出半声。
“刘向,你胆子不小。”容恕洲看他的眼神冷峻漠然,教人揣度不出意思。
刘向其实消息十分灵通,也够油滑。
自从得知冗虚汲垣得了圣尊青眼,刘向就一直在暗地里准备,把那少年教养成最像戚涣的模样,一举一动几乎分毫不差。
但他却有戚涣所没有的,一具从没被人碰过的身体。
毕竟谁不知道,冗虚派倒下之前,戚涣可是个千人骑万人踏的奴。
谁没见过他赤裸辗转的模样?
床上手段再淫靡魅人,也不过一晌风流,人间男子尚不愿去折那曲江临池柳,容恕洲身居高位,如今天下几乎无人敢轻易与之争锋,更不可能不介意从前的事。
他知道容恕洲与戚涣互相心悦,可普通婚配尚且有三妻四妾,何况是龙阳断袖之癖,哪有男人会不偷腥?
那少年的确很像戚涣,就连斟茶时微微外偏的小指都一模一样。
但是刘向不知道,那是因为戚涣曾被生生钉碎手指,断骨重接,才有了那轻微的不协调。
就像刘向不明白,容恕洲喜欢,是因为那是戚涣的样子,而不是因为戚涣像他喜欢的样子。
很多事,也不是有没有人知道,戚涣会不会知道的问题。
哪怕有一瞬生了半点不该有的心思,容恕洲自己就不会饶过自己。
容恕洲给自己倒了杯茶,语气平淡无波。
“我本想留你多活几天,可你非要撞到我面前。”
那张泛着油光的脸灰白下来,两股战战濡湿,刘向腿一软跪倒在地,趴在地上拼命磕头。却在将要哭嚎时被容恕洲掐断所有声响。
刘向多年豢养奴宠,将这些年幼的孩子调教得顺从乖觉不敢反抗,然后送到那些“德高望重”之辈手里,等这些人玩腻了,再把人带回来处理掉,绝不让他们能有机会漏出一星半点。多年来,他们就靠着这样“体贴”的服务来换得宗派立足的一席之地。
其实无论刘向做什么,容恕洲也不会让他活,寻了最错的一条死路,不过是他更快得给自己敲了丧钟罢了。
傀儡把杀猪一样嘶嚎的人拖出大殿,透明的蝴蝶从容恕洲袖中鱼贯而出,顺着殿门飞出大殿停滞在半空,密密麻麻不多时竟铺满天际,看得人头皮发麻。容恕洲抬抬搭在茶盅上的食指,那些溟蝶就颇有次序地朝着各个方向四散而起,转瞬消失在远峰之上。
空旷的大殿里,容恕洲微微低着头,不知在沉思什么,过了半晌,他抬头看看已断的更漏。
出了这档子事,让他很想他。
戚涣倚在一处阑干上,看着天上零星雪花飘下来,在地上积起薄薄一层,剔透璀璨,天地也因此亮了一点点。
他一身荼白朗如皓月,倒是胜雪三分。
他没有看完,因为他当然信容恕洲不会留下那个孩子。
可他明明知道如此,在看到那个场景的一瞬间,心里竟升起无可抑制的疯狂。
他想把容恕洲藏起来,藏到一个没人找得到的地方,不让任何人对他有半点非分之想。
他憎恶这样的自己。
这样的控制欲,几乎与他那个好徒弟如初一辙。恶心又扭曲。像一头压抑在内心最晦暗的地方的狰狞凶兽,散发着腐朽的恶臭。
夏声也说爱他。
那他呢?
他在做什么?
戚涣低头看着手中花纹复杂精巧的手炉,这是容恕洲亲自买的,在人间银铺里挑了半个多时辰。
那天容恕洲说要挑一个最好看的,以便能勉强衬得上他一点。
不过是一个物件。
容恕洲好像特别热衷于这种小物件,手炉,玉佩,折扇,他眼光很高,往往看中那些天工造物鬼斧神工之物,千辛万苦也要寻了来。
他原以为是容恕洲自己喜欢,可寻来后,容恕洲都林林总总送给了他。
容恕洲说,只是觉得寻常物件配不上他。
戚涣把手炉放在一旁台上,岁暮天寒,他有些犹疑,指尖不忍离了这唯一的暖意。
你看,你连一个手炉都没有勇气放下。
可笑如此。
容恕洲不是他的一个物件,这样扭曲的控制欲,对容恕洲来说并不公平。
自从那天容恕洲一字一句地告诉他“你还有我,我是你的。”
为了让他相信,容恕洲甚至戴上了象征“依附,所有”的银链,上面刻着他的名字。
那是为奴之人,或是人间被包下的小倌,才会戴的东西。
每天那么多人造访,容恕洲却毫不掩饰。
那些人眼里的惊疑,探寻,鄙夷,他看得清楚。仙界关于此事的传闻,偶有淫秽到不堪入耳,他也不是没听到过。
可他做了什么?
他从未提过一次让容恕洲把那东西摘下来,哪怕明知那是一种折辱。
哪怕他自己明知那些有多难熬。
无耻至极。
戚涣低头,长睫上落了雪,晶莹剔透。
戚汲垣,你还想要什么呢?
像你那好徒弟一样自私又恶毒地伤害每一个人吗?
你厌恶他,可你多像他。
你凭什么呢?容恕洲不过倒霉喜欢上了你。
无边涌上的自我厌弃让他想冷笑,想讥讽,想说最恶毒的语句,
给他
自己。
自嘲地笑笑,戚涣放下手炉,近乎自虐一般地拂过结了冰雪的白玉阑干,握紧满手冰碴,逼自己体味着这难以忍受的刺痛,冰化了,握不住,从指缝里流下来,苍白的手中一片冻伤的殷红。
雪落在手炉上,从那银白的缝隙间落下去,溢出一点青烟后,化作片片劫灰。
不知站了多久,一直到被吞噬全身温度,几乎没有了知觉。
该回去了,再不回去,他要担心了。
“阿涣。”
戚涣转过身,看见容恕洲站在几步远处,蹙眉看着他。
容恕洲见戚涣迟迟未归,以为他被什么事绊住了手脚,没想到听说他未及戌时就回来了,还带了酒。
果然看见他白衣胜雪,半倚着阑干,周身罕见的闲散恣意,皎皎如玉树临风,朗朗如日月入怀。雪光落在肩上,给他镀上了一层莹白的光晕。
那这近三个时辰,他就一直站在这寒风里?
做什么?
看雪?
这不到一寸厚的雪有什么看头?
“在这待了多久了?”容恕洲忍不住问道。
“没多久,我刚回来。”
看容恕洲没有说话,又补了一句。
“我就是看看雪。”
容恕洲轻轻叹了口气,看了眼戚涣近乎湿透的披风,不动声色。
戚涣根本不知道,他真正放松的时候,是很少笑的。所以只要他戴上了这“戚涣”式的,堪称完美的,画皮一样的笑容,容恕洲就知道他绷紧了神经。
看他这样,容恕洲不舍得再过催逼,屈起手指拂下了他肩上的雪。
“先回去。”
戚涣却施施然放下手炉,倚在了阑干上。
他从纳戒里取出一个精致的稠袋,解开袋口里面是一个六角青铜牌符。
戚涣目光很空,像是在看容恕洲,又像是越过面前的人在看更远的什么。
树上有处枯枝长得密,上面压着完整的一片陈雪,正在风里无可避免地缓慢滑落。
那个六角的牌符在戚涣指间翻了个转,那东西做的很精巧,戚涣专门雇了整个浑坊来铸造,整整花了小半旬才选出一个满意的。
但那东西再漂亮,任何人一眼看到也绝不会以为它是个装饰。
这是臧。
奴契分生死两类,臧是死契,一旦烙下,哪怕死了烂干净剩下一摊骨头上都有印迹。
戚涣肩上原本有一个,后来被他生挫了下去,那种疼现在想起也觉得难熬。
戚涣把臧做成了项坠,当然没了契约的作用,但奴契就是奴契,再怎么镶珠裱花也不会有第二种意思。
“带吗。”
不过两个字,在他齿间磕得咯吱作响,戚涣近乎发狠地盯着容恕洲,泛着绯红的指尖轻轻战栗。
他是个疯子,畜生,戚涣搜肠刮肚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留给自己。
他极力地表现出一种轻挑放纵,但没有谁比他自己更清楚,他想让容恕洲带上,他想给容恕洲烙下这样一个印,无数场旖旎大梦里,他将那些曾让他自己都恨不能求死的法子都加诸在容恕洲身上,他看他痛苦,看他绝望,他把他困于这一方狭小天地。
或许有的人骨子里便恶,上苍的苛待是过早的仁慈,给了他们一个溃烂的借口。
他应该告诉容恕洲的,那些骇人的,自私的,恶心的,压抑着的想法,他都应该告诉他。
让容恕洲知晓一切后,再决定还要不要他。
容恕洲并不怎么在意这些,不过一个物件,不痛不痒地戴着就能让戚涣少怕几分,他觉得没什么不好。至于旁人言语更到不了他眼里。
戚涣呼吸微弱促急,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明明一个落拓懒散的姿势,硬是显现出一种微妙的紧绷,整个人都像只被吓歹了毛的小兽,抱着尾巴犹还逞凶斗狠,发出近乎企求的威胁。
容恕洲微微低下头,繁复的银链映出森冷的雪色。
戚涣难以置信地看着他。
“不是挂在这上面吗?”
容恕洲未等来动作,疑惑地抬起头,温热柔软的气息流淌过两人之间,转瞬卷进了风里。
戚涣突然猛扑过来,扯着容恕洲的衣衿把他拉向自己,玉阶上湿淋淋都是雪,容恕洲毫无防备地被他用力一带竟没站住,两个人一起滚到化了一半的雪里。容恕洲护着戚涣的头,后背砸在了树下一条凸起的老根上,瞬间被雪水浸透。
树上枝杈受了牵连,承着的雪终于扑簌簌落下来撒了树下的人满身。